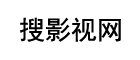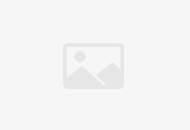作者:孔敏(Maja Korbecka)
译者:易二三
校对:覃天
来源:easternkicks.com(2023年3月27日)
在今年的柏林电影节上,中国电影的身影又开始活跃起来。其中,张大磊也在凭借短片《下午过去了一半》(Day is Done)获得评审团银熊奖(短片)之后,再次来到柏林。此次,他带来了两部新作——短片《我的朋友》(All Tomorrow’s Parties)和根据双雪涛的同名小说《平原上的摩西》(Why Try to Change Me Now)改编的爱奇艺原创剧集。
我们谈到了声景在他电影中的作用、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共同遗产,以及对20世纪90年代初的重现。当张大磊提到他青少年时期参加摇滚乐队的经历时,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每次听到他的作品的英文片名,我的脑海中就会立即响起相应的旋律——地下丝绒乐队的《All Tomorrow's Parties》或尼克·德雷克的《Day is Done》。
问: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出国学习电影。通常的目的地是英国、美国或法国。但你选择了俄罗斯。我从未见过在圣彼得堡学习电影的人。你为什么选择了那所学校?
张大磊:进入圣彼得堡国立影视大学学习有点出乎我的意料。这其实是一件非常个人化的选择。高中时我非常喜欢摇滚乐,参加过各种乐队。为了能做自己的事情,我决定退学。离开学校后,我突然意识到这可能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开始怀疑自己:搞什么摇滚乐,搞什么乐队?于是我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我根本不需要离开学校,但一旦离开就回不去了。
张大磊我开始考虑出国,换个环境。我的家乡呼和浩特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邻近俄罗斯。前几代中国电影人和艺术家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苏联文化的影响,很多人都去那里学习,甚至有些人早在30年代就去了。这在某种程度上给人一种熟悉的感觉,当然也明显十分不同。此外,圣彼得堡一直是俄罗斯的文化中心和艺术之都,这也是我决定去那里的重要原因。
问:那所大学的课程应该都是俄语教授的吧。你在哪学的俄语?
张大磊:去俄罗斯的第一年,我一直在距离莫斯科约200公里的图拉学习俄语。图拉离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很近,而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出生地和故居。在图拉的那所语音学校里,70%的学生都是中国人。一年内完成语言学习后,我一个人跑去了圣彼得堡国立影视大学。
问:你的父亲张建华是著名编剧,在电影制片厂分配编制之前,你就在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度过了年少时光。90年代以来,中国各地方的电影制片厂都经历了改革,转变为电影集团。他们也开始重新制作电影,《白塔之光》就是最新的一个例子。不过你的所有电影都是由爱奇艺出品的,我很好奇你有没有考虑过跟这些地方电影制片厂合作一部电影?
张大磊:中国的电影制片厂在电影史上做出了巨大贡献,每当我们观看老电影,看到西安电影制片厂或内蒙古电影制片厂的标志时,都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情感。问题是这些电影制片厂已不复存在。正如你提到的,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这些电影制片厂变成了电影集团。
《白塔之光》(2023)现在,他们的工作方法、制作方案、设备设施,全都不一样了。如果我们能回到电影制片厂时代——我说的不是电影集团——我当然很乐意。事实上,我很愿意回到那种氛围,因为我从小就生活在那里,我总觉得电影制片厂制作的东西更纯粹。电影制片厂的工作人员都住在一起,都拿着国家的工资,所以他们可以真正专注于电影制作。
他们可以选择是赚钱、获奖,还是创作艺术。他们可以进行尝试,而不必花费大量时间向不同的投资者推销自己的想法。过去,制片厂里的每个人都有固定的工资,无论他们是否在拍电影。如果他们有活干,每天还能额外得到一点补贴。老电影制片厂的日常生活非常有趣。
问:你的电影一直在描绘90年代初的场景,你是如何再现那个时代的?
张大磊:我非常喜欢90年代,包括那个时候的生活方式、氛围和流行等等。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回到90年代的生活方式,身边塞满那个时代的物品。我常常收集画册、照片、磁带、CD以及衣服。我对90年代非常着迷。因此,在拍摄以那个年代为背景的电影时,我并不是从零开始的。
《八月》(2016)有些导演拍摄年代戏时,他们需要重新调查和积累物品,花时间寻找道具和服装。但我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我一直都沉浸在那个年代。此外,我们的艺术指导兰志强——他是我们在银幕上重现90年代的关键人物,他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研究和收集那个时代的物品。
至于美学, 90年代的中国与当时的苏联和波兰颇为相似,都经历了快速的市场化和巨大的社会变革。我看了很多东欧电影,也去过那里旅行,它们给我的感觉很舒服,而且能从中闻到一些熟悉的气息。我并不是想学习什么再现当地文化的特殊技巧,我只是喜欢阅读文学作品、聆听后社会主义国家的音乐所带来的感觉。我几乎每天都听苏联老音乐,偶尔也听波兰音乐。
问:我对这种后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共同遗产的感觉也非常着迷。我在上海读书时,室友是一个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女孩。有一天,她安静地哼了一段旋律。我感到非常惊讶,因为这段旋律也被用在我们波兰耳熟能详的一首老歌中。
张大磊:还有很多古老的德国曲调。旋律可以跨越国际,只是语言发生了变化。在中国,有许多歌曲的旋律来自苏联或东欧音乐,只不过歌词是中文的。
问:在中国,大家对于后社会主义国家共同遗产的讨论多吗?
张大磊:这是一个小众话题。不过,它也非常有趣,因为这个话题吸引了一些人,让我们能够自发组成一个社群,在其中讨论音乐、文学和历史。总而言之,人们有兴趣谈论共同遗产,但它并不是主流。我们这些80年代出生的人现在已经四十多岁了。
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很难想象上世纪最后一二十年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因为他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已经大不相同了。而我们当时还处于青少年或儿童的阶段,所以在我们的回忆中那是一个黄金时代,因为我们没有承担太多的社会责任。我们不必冷静地分析那个社会发生了什么,我们只是体验这个世界。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回忆,我们很幸运能拥有这些回忆。
问:你的电影中一直都有对黄金时代的憧憬。这让我想起了侯孝贤的一些早期作品,比如《冬冬的假期》。你还常常都通过媒体——旧电视和广播节目——重建那个时代的各种细节,能谈谈你的电影中对声景的设计吗?
张大磊:声音在我的创作中非常重要。我曾与其他电影人讨论过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灵感来源。对有些人来说,文学作品会带给他们灵感。对其他人来说,新闻或当前的社会事件是创作动力的来源。我的灵感往往来自于一种声音或一首歌曲。
因此,在每次创作之初,都会有一种声音为我创造出一个空间,让我想象一个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人物会有什么样的声音。对我来说,声音是去功能化的,不像在经典剧情片、动画片或恐怖片中,声音应该让观众有某种感觉,或者必须传递明确的信息,如台词的戏剧效果。
《冬冬的假期》(1984)在我的电影中,声音就是声音。对我来说,电影中的声音更多的是关于空间的完整性和真实性。我会在剧本中记下所有的声音,包括影片中出现的大部分歌曲和音乐。我还需要录音师先做一个简单的声音设计,判断在电影空间中能听到什么声音,场景有多长,以及如何将这种设计与录音结合起来,达到想要的效果。
问:你提到了声音的完整性和真实性。我常常觉得影像很容易欺骗人,但声音就不是。我们对周围的声音非常警惕,也许这源于我们的祖先在野外生活的经验。
张大磊:特别有趣的是,影像的局限性太大,我们只能看到眼前的事物。但声音却能让我们意识到离我们更远、我们无法触及的环境中存在和发生的一切。纯净的声音带来的这种空间感特别强烈。它可以取代许多额外的叙事手段,如台词或画外音。声音会带来情感。
问:说到声音和音乐是讲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你的电影中,经常会有一个演奏乐器的女性角色。这是为什么?
张大磊:首先,我很喜欢音乐,也想在我的电影中加入音乐,但我更希望使用以电影空间为基础的声景,避免画外音。我希望这些旋律和音乐能够自然地存在于内容中,所以我一定会写放一些声源进去,有时是录音机,有时是音箱,有时是会演奏乐器的人。
问:你的新短片《我的朋友》以特吕弗的《四百击》的最后一幕结尾。其中的音乐总是能触动我的情感,它是如此震撼人心。我想请你谈谈这个场景,因为我不知道在工厂放映法国新浪潮电影是否常见?
张大磊:这其实是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在中国电影中,有许多信息被放在电影空间中的标语和广告牌上——还有很多字幕没有打出来。事实上,短片的故事发生地不是在工厂,而是在电影制片厂。在一个场景中,地板上扔着票据,上面写着「青山省电影制片厂」。在80年代和90年代,这些影片一般人都无法看到,只有电影学院和电影制片厂的人才能将其作为内部参考影片用于学习观摩。
问:拍摄《我的朋友》这样的短片似乎也非常困难,因为20到30分钟的时间框架带来了很多限制。而拍摄《平原上的摩西》这样体量的作品也需要很多技巧,你可以讲的内容更多,但同时要很好地平衡整个画面和把握讲故事的节奏。你的电影往往会回到过去,重现事件。你是否考虑过拍摄一部以当代为背景的电影?
张大磊:我还没有尝试过,但也许没有必要用时间和年代来划分我的电影,因为归根结底我还是在追求一种味道。当我这样做时,我会觉得很快乐。事实上,要把握当代的味道并不太容易,因为它还在酝酿之中。因此,我还没有选择以当代为背景的故事。如果要描绘空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生活方式,那是很困难的。
这种对味道的追寻与回忆的感觉有关。如果事件发生在最近的过去,就不可能形成这种联系。我着迷于探索以记忆为媒介的现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当你怀疑某件事情是否真的发生过时,你会感到困惑。这种感觉有时如梦一般,特别迷人。
《平原上的摩西》(2023)问:我常常惊讶于我们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我们当时所处的空间之上的。你的电影中总是有发生在室外游泳池的场景。这背后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张大磊:在八九十年代,中国只有室外游泳池,所以游泳几乎是专属于夏天的活动。如果我选择在冬天拍摄,电影中就会有在溜冰场的场景。以前,一切都要根据季节变化来调整。有些蔬菜和水果只在冬天吃,有些只在夏天吃。冬季运动和夏季运动让四季各具特色。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特点之一,大家聚集在一起,共同参与一项活动,分享一段记忆。夏天,大家都泡在游泳池里,然后晒着太阳。仿佛置身于海边。
问:现在,我们似乎有了无限的休闲选择,但许多人却觉得自己被孤立化了。我记得自己在这个世纪初的波兰也有过同样的感觉,夏天等着吃草莓,去公共游泳池一玩就是一整天,还有奶油和巧克力威化饼的香味。说到跨国经历,你对未来在其他国家联合制作和拍摄电影有什么想法吗?
张大磊:《蓝色列车》是在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拍摄的,与中国仅一墙之隔。我手头的确有一个合拍片的项目——另一部在俄罗斯取景的电影。不过,我很想去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拍摄。
《蓝色列车》(2020)问:你现在有正在制作的新片吗?
张大磊:我想今年在呼和浩特开始拍摄一个新项目。不过现在还没有完全确定。这并不取决于我,而是取决于我们能否及时找到足够的资金。这个项目是《八月》的延续。
它的灵感来源于我2000年18岁时的经历和当时中国的摇滚乐坛。故事将围绕一位退休的老诗人和一群知识分子办的报纸展开。随着互联网的逐渐兴起和普及,人们不再阅读报纸,编辑部也被迫关闭。这部影片将探讨这些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