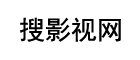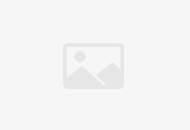王一凡(艺术家)的个人简介
王一凡,1978年生于北京。200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现工作生活于北京,中国当代青年艺术家之一。
展览
个展2011
塞翁持火,星空间,北京,中国
2009
看不完,星空间北京
2007
一张叛离的画儿,星空间北京
群展2012
解禁之后,星空间,北京,中国
2009
新作,星空间,北京 ,北京,中国
从Zero 到Hero,星空间,北京,中国
时间的能量,昌阿特,北京 ,北京,中国
艺术北京,农业展览馆北京,北京,中国
2008
找自己,民生当代艺术中心,上海,北京,中国
2007
抽离中心的一代,798 艺术区,北京
第一届威尼斯双年展,网络展出
宋庄艺术节,宋庄 北京
2006
坏孩子的天空,星空间,北京
2005
第二届成都双年展――世纪与天堂,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成都
2003
汇合,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北京
出版
2009
《王一凡作品集2003-2009》,星空间,北京,中国
2008
《找自己》,星空间,北京,中国
2005
《坏孩子的天空》,星空间,北京,中国
解读
在中央美院附中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时期,王一凡的作品还属于比较典型的绘画创作。但后来王一凡的作品换了种全新的方式进行创作,是一种在刷成黑色的画布上通过写一些文字来营造出类似“黑板报”的视觉效果。在画面上,他用幽默而轻松的口吻描述着与过往的情感、冥想以及和秘密有关的故事,看起来有点儿像小说,但大部分素材都是他的个人经历。这样的作品既有绘画的特点,又不是纯粹的油画,形式非常特别。用王一凡的话说,这一切缘于一个“玩笑”。但总体来说,王一凡的作品还是大多带有高度的个人化色彩,以及很强的叙事性。
王一凡作品的表达有着个人气息的自然流露,而非下意识的、策略性的表演,这源于他在语言表达上的天赋,并且这也让他很容易令与他有过接触的人印象深刻。在他的绘画、装置、录像甚至小说中,我们都能看到类似的表达的冲动,没有充分转换为形式结构的直接抒发使这些作品有着难得一见的单纯和拙气。各种媒介的叙事语言对作品情节的塑造控制着王一凡在艺术实践中的表达,他对于这个世界的朴素的认知方式使他惯于将创作落在可被讲述的实处,因此即便作品中带有情绪的那一部分内容,也是不难解读的。
“塞翁持火”是他对自己截止于目 前的状况的申辩和证明,也是王一凡的艺术实践中一个新阶段的呈现。作品中所倾注的价值观和判断无疑是与所谓的主流社会的取向相逆的,也脱离于我们所认为的当代艺术的上下文。在这个时代,现实主义的生存哲学是主流价值观形成的基础,对个人的评判在各行业内都有着量化的标准,艺术领域也同样如此。对于这样的现实,王一凡始终保留着客观的认识,在“所得”和“所失”之外寻找对自我来说更为永恒的价值。他唯一能够证明这种价值的方式就是用作品来描述它,并且唤醒它在他人意识中的投影。“塞翁持火”是王一凡结合中国成语“塞翁失马”发明的新词,“塞翁”在这里被艺术家用来指代成语下半句里“焉知非福”的不确定状态,反省了功利社会过于短视追求“得与失”的态度,表达了艺术家一种辩证的世界观。同名绘画作品描绘了一位耄耋老公手持火柴的形象,象征能量的火和这位叫塞翁的老头其实是艺术家自己现实生活状态的一种譬喻。其他几幅绘画的主人公也多出自艺术家的朋友或是他故事脚本里创造出的人物。绘画对王一凡来说,更重要的是一种讲述故事和传达观念的载体,写实的风格之下,却是艺术家极为个人化的对时间以及人性的探讨。
王一凡所选择的材料具有一些天然的和日常生活的关系,比如浴缸、垃圾桶、飞机模型玩具以及儿童假人模特,它们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标记着断裂的时间节点和对终极意义的追问;就像王一凡的装置作品中有的一种含蓄的直接,会有点中国古代文人山水的味道,表面宁静却在身后暗含时代的奔跑与社会的喧嚣;而出现在绘画作品中的情节则在故事性很强的题目中有明确提示,这种关联所带来的趣味暗示使观看变成了阅读和猜测。
在由叙事串联起来的一系列表达中,我们可以看到王一凡的工作方式是非常个人化和浪漫主义的,这种方式很明显地与更大范围内的讨论保持距离,是对个人的直接社会性的不自觉回避,正如同“塞翁持火”这个自造词,他在难于辨别方向的摸索中独自照明前行。
解读艺术家
在一次布展中,王一凡指挥调整悬挂“黑板”系列作品悬挂高度时的背影给人的印象很深,头戴黑色鸭舌帽、身着蓝色宽大T恤衫的他乍一看就像是一黑一蓝两个方块拼出来的一样。让人想到曾经在陈丹青工作室画画,在黑色画布上写故事的那个男孩,现 在的他已经在用这些“黑板”来进行创作。
王一凡头脑灵光,不仅有着可以用两只手同时绘画的才能,童年时也是数学小奇才,并有家里堆积的奖品为证。不过长大以后他更像个“坏家伙”,每天大吃大喝玩命找乐。他愿意把他所谓“男人”的一面公开展现, 因为他希望成为一个够“man”的艺术家。
王一凡还有着属于他的独特文字天赋,如他的《怀念》系列就是模仿小时候“写在黑板上”的惩罚。王一凡有着幽默而轻松的口吻,并在绘画中以此来描述着与他过往的情感、冥想以及和秘密有关的故事。也许他也清楚,很少有人会真正地把黑板内容看完,因而他的北京话和潦草的书法给了读者增加难度,但是王一凡从不会为了让他人容易接受而改变自己的作品。
王一凡生活在艺术圈的边缘,靠教书和打零工维持生活, 他甘愿做各种艺术试验而不顾市场的反馈――试验是为了满足他自己,而在他找到的独特艺术语言中,却折射出北京街头的反论真理。如在他的DV 作品《监视时间-王一凡的钟表》里,拍摄90 年代中国普通家庭必备的石英钟,用一天的时间纪录了石英钟的状态,并用特殊而隐蔽的方式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在这漫长的时间里, 镜头丝毫没有切换,观众不太可能坚持把作品看完,但观看作品的不同时刻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就像在面对“真实”。
王一凡个展评论
文 佚名
起初干上艺术这一行,王一凡并不是很情愿,虽然他爱画画,但是他更习惯作一个街头朋克。这也是我们为他的首个展览命名的原因:一张叛离的画儿。
“一张叛离的画儿”的主线是怀念,王一凡在画布上歪歪扭扭地用文字描述着一个个与他过往的情感、冥想、秘密有关的故事,就像是用一块块布满文字的小黑板在向世人公布着他的隐私。
在星空间举办的此次展览还包括王一凡连续拍摄24小时不间断的DV作品――“王一凡的钟表――监视时间”以及名为“在窗子里”的系列装置。在这个系列装置当中,王一凡选取了从拆迁工地中捡来的破窗户配以影像,形成了“在窗子里”的作品。实际上,他毫不避讳的用方言和调侃表达了作为北京人的一种“土气”。
蘸满了北京味儿
除了通篇洋溢的北京方言,王一凡似乎并没有明确的目的,他就是一“糙人”,心直口快。他一肚子坏水儿,但又让你觉得有情可原。
王一凡的作品是对主流绘画模式的一种挑衅,他极大的贬低了对于传统意义上“绘画”的重视和强调。同时他对自我形象的戏虐也是对艺术界大腕儿和理想主义者的一种嘲讽。
王一凡聊个展
王一凡:这次展览的这些画都是2010年到今 年8、9月份画的,画里面有些是我的朋友给我当的模特,画的内容是我暂时编的小故事。有可能是我画这张画时故事存在,但再画下一张时第一张画的故事我也不记得了。
有一张画叫《找不到电台的人》,这个名字与我从小听收音机的经历有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总是想从电台里听到一些消息,在漫无目的的调电台,最后什么也没找到,并没有听到真正能感兴趣或打算听到的消息。但这是一个等待和找寻的过程。
还有一张画叫《找到了电台的人》。由于我画了一张叫《找不到电台的人》,我觉得这样不太好,既然找不到电台,但人的愿望还是希望能够找到电台的。所以我画了一位老人,给了一个时间的概念,最终还是找到了电台,算是具体体现在我画面里的一个善举。
另外一张画叫《新闻倾听者》,它与我生活的感觉还是相关的,其实我最初不是自发的,被家里人带动,离不开新闻。直到现在只要一播放新闻,我就觉得不能错过,要坐在那里听。但听到的消息我也不知道靠谱不靠谱,是真是假也不清楚,但还是会一味的听下去,总觉得听比不听强,会掌握到别人没有掌握到的信息及对将来的预计。我觉得好多生活并不是非常如意的人,其实他们总是希望在新闻广播里找到自己的可能性。
最 近完成的一张画叫《塞翁持火》,这张画我没有找周围的人当模特,因为我觉得它比较像我的一个生活状态。因为这两年父母包括亲戚朋友总在与我聊,我所失比较多,但没有所得。但我觉得这事不能这样说,我觉得我还是有所得的。虽然我也解释不清楚所得是什么,拿不出来证据堵别人嘴,但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塞翁失马》这个故事,其实人预计不到你面前的所失所得对你下一步有何征兆。这个故事其实帮我抵挡了很多别人的劝说或批评,所以我就画了这一张画。
我对火比较感兴趣,火其实是一个能量的代表,是破坏也好,还是重构也好,都需要能量作为背景。
谢墨凛:有破坏与期望同时存在的一个矛盾。
王一凡:并不是想说矛盾,想说的是它代表了一个能量,这个能量存在时就有无尽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有可能很好,有可能比较悲催,这都没准儿。但它有能量,在人能理解的范围内不就是有大于无嘛。
《调和者》画的是一个人拿着两瓶药水,一个红色,一个蓝色,在往试管里的倒,这个人物也是我的一个朋友。这个人的脸长的比较怪,特别宽,尤其他脸盘特别大,又有点褶子,因为常年喝酒不睡觉,总有疲惫在脸上。再加上脸盘大把疲惫劲也给放大了,我觉得挺好。
一般我画一张画,不是先想构图,而是会先想我大致画的内容是一件什么事。有时我会特别喜欢关于新闻的一句话,像《新闻倾听者》之类的这种东西。这时我就基本能察觉出这张画的情调应该是怎样的。
谢墨凛:比如色调呢?
王一凡:在大学里就比较喜欢暗颜色,我记得有一件事我小舅舅对我打击特别大。中国有一段时间流行算命,他那时也练气功、算命。有一天我没睡着觉,我听见我小舅舅特别认真而且着急的跟我妈说,说给我算了一卦。
谢墨凛:关于你的?
王一凡:对。他说:“一凡将来不会是一个深刻的人,应该比较浅浮。”当时我一是惊讶连这也能算出来,还有就是害怕。最后我发现我在大学里还有这样的担忧,因为大学里你与社会不沾边,不知道自己深与浅,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后来我说我这个画暗一点吧,最起码能遮一点浅浮的劲儿。
《斑斑》是垃圾桶旁边有一个小的塑料模特。这个塑料模特其实就在我现 在住的地方不远的一个比较便宜的衣服摊门口放着。我当时问了,他也是从别人的废品那里拿来的。这个模特模型是我记得是很小的时候,国内一大批模特都是这样做的,浓眉大眼,将亚洲人的脸形稍微做出点洋味儿来。在我看来,这模特会带来当年兴盛一时,但如今已被遗弃的一种感觉。我还想起来小时候看《铁臂阿童木》的小人书,我记得那时看了一集后哇哇哭,特别难过。看到阿童木没有能量,最后走投无路,沉到水底被遗弃了。尽管这时一个机器人丧失动能以后,它什么都不是,但它还是有很完美的造型。并且新一代机器,坏科学家也都在不断的出产新发明的东西,当时看的我特伤心。当看到这个模特后与小人书里面的情结就拼接到一起了。我就觉得我要把这个东西买回来,代表我的一种很强的感情来展示出来。
我当初在想这个东西应该与什么放在一起好,想了半天,最后我觉得直接将它放在垃圾桶边上比较好,直接提示它即将进入的是垃圾桶。它所述的感情还是很通俗的,大多数人都存在的,对时间和爱惜的东西即将逝去的一种担忧和怀念。
《旧澡盆镇的机场》,这里面其实也有我的经历。有次我去姥姥家,他们说我太脏了,得好好泡一个澡。这时我就知道我要泡很长时间,在里面也不能干泡着,我会带玩具进去。各种飞机、汽车、船,只要是不怕水的我就一块带了进去,一边玩一边泡着。这样出来也就干净了,而且我觉得玩的挺好。我就把当时玩儿的方式用现 在理性的一种思维重新归纳了一下,我觉得当我在里面玩飞机的时候,澡盆里当摆满飞机时就变成了一个机场。但一个机场不可能在澡盆里,必须在一个能足够盛得下的地方。我觉得能容纳一个机场最小的地点概念就是一个镇。既然这个澡盆是一个镇,那这镇周围应该有点像那种地脉山丘的东西,所以我就将周围用土拢起来。由于它是旧的,所以就给它起名叫《旧澡盆镇的机场》。我做这个是自己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比如我爱给别人起外号,或改课文,或给一首诗添句子或进行删改,我记得谢墨凛就说过,说我多少有点妄想症。“澡盆镇”其实是我按着一个概念来回来去连着改了三、四层概念,就觉得一下子就得到了抒发。
王光乐:我觉得他有叙事的天分,包括我觉得他现 在已经动用了好几个媒介,但我觉得都属于叙事艺术。实际上你每个题目的下面都在讲一个故事。
(《焊接1》是一件王一凡自己也解释不清的作品,对形式的直觉在这里起了更大的作用。)
王一凡:不是有一个词叫“格调”吗,有好多人要追的那个东西。如果我有一个格调的话,我觉得它在我的床头就能把我的格调显出来,就这么高。
关于不同创作语言间的互补
大学一毕业,不会画画的感觉就来了。有一阵发现我越画越不好,心想画的东西都画不出来,就连过去在上学时会的那一套自圆其说的东西也丢了。但那时心里也明白不能就此罢手,于是就想干别的。当然不会脱离艺术。我就想先不画了,去做装置,开始做的时就觉得有一种比较舒服的东西来了。这种形式不管在视觉艺术里存在多少年,但在整个人的范围里欣赏来看还是一个新的东西,还不是所有人都看臭了街的东西。它使得那些很必要的,但又被太多人说烂的感情,又可以重提了。因为它的载体变了,内容也让人感觉焕然一新,好像重新充电一样,也不让人反感了。
谢墨凛:这期间比较满意的作品是什么?
王一凡:我对《监视时间-王一凡的钟表》和《等候全天的雨在窗子里》都挺满意的。当这种表达一次接一次,最后很自然的时候,然后有一天我发现,再回到画面时可能就不紧张了。我也不用想画面上有多少不该往上放的东西,只要把我能说的那点事画上去就可以了。
朋友眼中的王一凡
王光乐:我最感兴趣的是你这个人。跟我一直在思考的意识形态这个问题特别有关系。你向来我行我素,特别鲜活。我觉得特别是上一代人可能会觉得,接下来我们该怎么过日子,该怎么样。好像你从来不做这种事。
谢墨凛:你需要全面的慢慢成熟也好,如何面对整个社会的压力也好。其实社会压力在你身上还是有体现的,你不完全能够免疫这个东西。虽然你在尽量避免别人把你拉到他们所希望的队伍里去,但这对你的生活冲击还是很大的。
王光乐:你绝对没有分析性的想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吧?
王一凡:没有。
王光乐:对,他绝对不会这样去想,因为他就是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搅碎了的一个整体。我与王一凡经常吃饭,他从来不与我聊艺术。这里就包含了那种完整,有一种自主度在里面。就我2004年到现 在的观察,我觉得他就是一个个体的样板,特鲜活。他清楚,比如人与人没有可比性。
王一凡:开始画画时,其实我是凭空说的,一笔没画。我和谢墨凛说,我想画画。他问我想画什么样的。我说我想画的画并不新,不是要找一种新的画面感,但也不是传统的东西。如果说我给画做过一次具体的设计就是在这时。因为将这个东西放得不偏不倚,往往大伙儿会容易忽视这种状态,但这种状态对我特别重要。因为首先我确认了我想被人知道的东西和这个事关系并不是太大,但是我又不能让我的画太新或者太传统。如果那样会被人强行的放在一种刻意的观念里思考。这样可以把两边都躲开,不声不响的表达出来。
王光乐:他的语言不新不旧,旧的语言是成语,新的语言可能是我们的网络用语。但是他还是他,他就是操着自己的口语,带着自己的直觉感受的东西来画。这种东西非常的缓慢,有待他持续再持续的一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