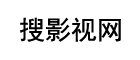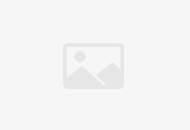吴文慧的个人简介
民盟成员。著有论文集《红楼梦新评》,专著<阿q真谛 专著 红楼梦研究史论 等获得多个奖项>个人简介
笔名:白盾、吴戈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22/5/5
民族:汉族
安徽泾县人。民盟成员。1944年肄业于上海法学院政治经济系。1949年前曾任屯溪《徽州日报》、重庆《商务日报》国际版编辑,1949年后历任宣城、巢县中学文史教员,安徽省文联理论编辑,徽州师专中文系教授。1943年开始发表作品。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论文集《红楼梦新评》,专著《阿Q真谛》、《红楼梦研究史论》、《历史的磨道》、《悟红论稿》、《三国演义纵横谈》、《浮生纪实》,论文《论鲁迅杂文的审美价值》等。专著《红楼梦研究史论》获1998年省社会科学二等奖,论文《红楼梦研究也要实事求是》获1978年-1985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论红迷――红楼梦魅力探源》获1986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创作经历
上世纪五十年代执教宣城中学时跻入研红领域。一九五四年秋白盾的红学论文《红楼梦是“怨而不怒”吗?》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白盾的文作于李希凡、蓝翎评红文章之前,发表时加编者按,被称为敢于向学术权威挑战的“小人物”,引起全国重视。
这以后,白盾先生调人安徽省文联担任《江淮文学》等报刊编辑。在《人民文学》等发表的《贾宝玉的典型意义》、《原型在阿Q造型中的作用》等文,均引起全国学术界关注。1957年后被划为右派并投入监狱,出狱后遣送回茂林老家,达二十余年。
八十年代白盾先生又活跃在文坛上,成为黄山学院文学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学术》、《红楼梦学刊》等国内主要报刊发表红楼梦研究、鲁迅研究、徽学研究及文学、哲学、史学理论研究等论文二百数十篇,230余万字;已出版专著《红楼梦新评》(上海文艺出版社,25万字)、《红楼梦研究史论》(天津人民出版社,50万字)、《历史的磨道》(安徽人民出版社,31万字)、《阿Q真谛》(天津人民出版社,26万字)、《悟红论稿》、(文化艺术出版社,28万字)等书。并撰有《三国论稿》、《胡适论稿》、《悟红二论》、《曹雪芹研究》、《明清小说论丛》等书稿多部。古代文学名著《红楼梦》的版本多达数百种。2004年12月由白盾先生审定并作序的新版《红楼梦》日前由黄山书社正式出版。这是一个让读者倍感亲切、而又引起学者注目的新版本――因为它是由黄山书社出版的、又因为有黄山学院部分师生参与了校勘工作,所以这个新版本被形象地称为“黄山版《红楼梦》”。深究起来,“黄山版《红楼梦》”在这一表层的含义之外,还有更深的内涵:它昭示这个新版本具有浓郁的皖派风格和皖派特色,像峻峭的黄山一样,在众多的《红楼梦》版本中奇峰突起。
主要经历
若以中国文化思想的传统而言,“小说”原本就是“小道”,向为君主士大夫所不齿。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记忆中,在公元1954那一年,一场针对俞平伯等人《红楼梦》研究的大批判运动,却是史无前例的重大政治事件。回顾当年,那场大批判可谓气势磅礴震撼朝野,无形之中已将红学研究等同国家政治,其地位至高至上无与伦比,只是不知曹雪芹、俞平伯等人的感觉如何――幸耶抑或不幸?
有意思的是,引发那场批判运动熊熊烈火的,竟是名不见经传的3个“小人物”。当时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红楼梦简论》以及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相继问世,引人瞩目。不幸的是,俞先生那种婉约晦涩的文字,周先生那种繁琐偏僻的考证,实在不合时宜;何况其中某些论点纯属旧式文人的一己好恶,混杂于那个时代旋律之中自然大不和谐。这就不能不引起一代热血青年的强烈不满。初生牛犊不怕虎,自古侠勇出少年。于是,他们操着尚不娴熟的“马克思主义的枪法”挺而发难,向新红学的权威提出了无畏的挑战。
白盾就是最早的那位挑战者。
红楼梦是怨而不怒的吗白盾的实名叫吴文慧,安徽泾县人,1922年出生。他对俞先生的《红楼梦研究》颇有异议。俞先生1952年9月出版的《红楼梦研究》,相对他1923年4月出版的《红楼梦辨》,虽然已经作出不少修改,但是修改并未伤筋动骨,诸多论点比如“作者自叙”、“情场忏悔”、“钗黛合一”、“怨而不怒”等等,可谓依然故我涛声依旧。其中关于《红楼梦》风格“怨而不怒”一说即引起青年白盾的强烈反感。时至1953年11月,《红楼梦研究》已经印至第六版,印数多达25000册,其畅销与影响使得作者“红”极一时。而正在那年那月,白盾写成一篇颇为尖锐的批评文章投寄《文艺报》,文章题目就叫《〈红楼梦〉是“怨而不怒”的吗?》
在白盾看来,黛玉的死与宝钗出嫁是同日同时,黛玉临终之际大声叫着“宝玉,你好――”这种情节大波大折、惊心动魄,简直是“怒发冲冠”,哪里是“怨而不怒”?白盾当时指出,俞先生肯定和赞美《红楼梦》的风格“怨而不怒”,其实就是肯定和赞美传统文化所谓的“诗教”,就是坚持具有封建主义性质的审美标准;这都说明俞先生灵魂深处蕴藏着一个欣赏“温柔敦厚”的精神上的“王国”。文章最后说,什么“缠绵悱恻”,什么“怨而不怒”,什么“温柔敦厚”……去它的吧!我们不要听它!(《人民日报》1954年11月12日)白盾认为:“怨而不怒”的风格是地主阶级“温柔敦厚”说的翻版……他说,贾宝玉这个形象所表现的“叛逆精神”,“它不仅u2018怒u2019而已,几乎可以说是个u2018蔑圣教、毁伦常、非孝道u2019的充满反封建色彩的闯将了”。(郭豫适《红楼梦研究小史续稿》第320页)
现在看来,白盾这篇文章自有几分幼稚、几分粗糙,不过当时却代表着不少同辈人的想法。他们的想法就是,绝不能以为“怨而不怒”说是“正确”观点,绝不能容许封建主义的幽灵借尸还魂!当然正如白盾自己所说,那时也并未真的认识到那是“资产阶级思想与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批判红学运动席卷全国在白盾撰文投寄《文艺报》之后的1954年春天,又有两位年轻人合作了一篇与俞平伯商榷的文章,那就是李希凡和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他们询问《文艺报》是否发表批评俞平伯的文章,因为没有得到答复,便将稿子发表在母校的《文史哲》杂志上。客观而论,当时两位大学毕业生尽管满怀激情渴望有所作为,但是他们发表的文章如同白盾的文章,都还属于学术商榷文章,发表的目的不过是期望引起红学界乃至学术界的注意而已,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奢望自己的文章会受到开国领袖毛泽东的赏识。然而历史的发展却超乎人们的想象。1954年9月《文史哲》发表了李、蓝的文章,10月16日毛泽东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指出,“这是30多年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并且迅速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批判运动。
深有意味的是,毛泽东在那封著名的信中特别指出:“事情是两个u2018小人物u2019做起来的,而u2018大人物u2019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其实正如前文所述,在两个“小人物”出场之前,已经出现一个“小人物”,那就是白盾。批判运动兴起之后,3个“小人物”的文章都很走红。李、蓝《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文艺报》转载不久,《光明日报》又发表了他们的《评红楼梦研究》。白盾原先已被《文艺报》退回的文稿,1954年11月12日发表于《人民日报》。这些文章在大报发表之后,全国报刊闻风而起纷纷转载,随即引发大量的批判文章,于是批判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
1954年12月8日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作出了《关于〈文艺报〉的决议》,针对“《文艺报》编辑部对于白盾、李希凡、蓝翎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批评俞平伯错误论点的文章”“拒绝刊登或不予理睬”的“错误”,决定作出“严肃处理”:“改组《文艺报》的编辑机构,重新成立编辑委员会,实施集体领导的原则”;同时还号召加紧扶植、大力提拔“新生力量”。
俞平伯在运动中作出了检讨,检讨自然十分认真,也有几分坦诚,并非完全违心。虽然不是所有批评都令他心悦诚服,但是不少意见也还切中肯綮揭示了他的弱点。俞先生后来继续发表《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出版《胭砚斋红楼梦评注辑录》、《红楼梦校本》等,足见他也并未因为批判而退缩,仍然坚持自己的《红楼梦》研究。
从当年小人物到今日红学家时过境迁,立足今日,人们可以平心静气地回顾当年的批判运动,可以客观历史地评论运动的是非得失。事实上人们已经这样做了,已经就那场运动作出了合理的评价。
试看当年,俞平伯认为《红楼梦》风格是“怨而不怒”这一论点,最初是遭到白盾的批评。其实我们现在可以说,那时白盾对俞平伯“怨而不怒”说的批评,与李、蓝对俞平伯“二美合一”说的批评一样,都有点类似唐·吉诃德攻打风车的情形,实际都弄错了自己攻击的目标,误将曹雪芹的观点当做俞平伯的观点而大批特批。所谓“二美合一”那是曹雪芹的构思,所谓“怨而不怒”那是《红楼梦》的风格,如此两项均不属于俞平伯的“创造”,而只属于俞平伯的“发现”。这样两大发现,当然属于俞平伯的研究成果、学术贡献。如此两项如果该批,那就该批曹雪芹,该批《红楼梦》,而不是批俞平伯。然而令人感慨的是,当时的不少批评,确实是外行批内行、无知批有知!批评者是一身正气,挨批者则委屈难言。今天我们在维护俞平伯的红学地位和学术名誉时,应该承认当年的荒谬。
回顾历史,是非终有公论;浏览人生,油然生发感慨。遥想当年,风云变幻,学术牵扯上重大政治,政治改变了几多人生!在那场大批判中,3个“小人物”一鸣惊人而意外走“红”,俞平伯经受着风雨冲击,而运动则成全了李、蓝二人。李、蓝幸运地调入人民日报社,成为中国第一大报的编辑。白盾却没有那么幸运。尽管他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发表的《红楼梦》研究文章都曾引起全国学术界的关注,但是不久却被划成右派,并被投入监狱3年,出狱之后遣回农村长达18年之久。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他被调到新建不久的徽州师专任教,重新投身与他久违的《红楼梦》研究。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白盾深受启发和鼓舞。他在《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发表了题为《〈红楼梦〉研究也要实事求是》的文章,从此步入他坚持实事求是、深入红学研究的新的学术生涯。
改革开放的30年中,白盾发表《红楼梦》研究等方面的论文近200篇,出版专著有《红楼梦新评》、《悟红论稿》、《悟红二论》、《红楼梦研究史论》、《曹雪芹研究》以及《红楼争鸣二百年》等多部,当初不为人知的红学“小人物”,今天成为名闻天下的红学家。
红学理论
两种版本,一名《石头记》,一名《红楼梦》,是两部面目、性质不同的书。如同有人所说“两部《水浒》,两个宋江”一样,也是“两部《红楼梦》”就有两个贾宝玉、两个薛宝钗、两个花袭人、两个尤三姐,等等。――即一个是为黛玉爱情割舍红尘、披着“大红猩猩斗篷”、仰天大笑出家而去的贾宝玉(程本),一个是“眼前无路想回头”、“骂死宝玉,却是自悔”的贾宝玉(脂本);一个是八面玲珑、上窜下跳地一心争劝宝二奶奶宝座”的薛宝钗(程本),一个是通情达理,能理解人、体贴人、帮助人,与黛玉“俨似同胞同出” 、谊结金兰的薛宝钗(脂本);一个是告密诬陷的“大观园的女特务”的花袭人(程本),一个是温柔和顺,善于体贴人、识大局的怡红院的“内当家”的花袭人(脂本);一个是“老辣无耻”、“淫了男人”的尤三姐(脂本),一个是冰清玉洁的“精神上的女神”的尤三姐(程本),等等。这之间,有着相互对立、水火不容的性质。程、高要将这样性质不同、面目有异的两部书,续改成性质一样、面目相同、前后一致的书,这是难度很大,难以做到的。他们显然作了很大的努力,不仅续写了后四十回,还对前八十回作了以照顾全书一致为目的的增删。
人物评价
白盾先生,首先因为他是著名的红学家,这当然不错。上世纪50年代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红楼梦〉是“怨而不怒”的吗?》,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贾宝玉的典型意义》,年轻的白盾就已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新时期以来,先生先后出版了《红楼梦新评》、《悟红论稿》、《红楼梦研究史论》、《红楼争鸣二百年》,加上尚待出版的《悟红二论》和《曹雪芹论稿》,论红文章专著超过200万言,早已成红学研究的一大重镇。在《红楼梦》文本批评、主旨研究、版本研究、作者研究、史论研究等方面,白盾先生均有辛勤耕耘及卓越建树。2005年由黄山书社出版,由白盾先生领衔黄山学院师生会校、以程甲本为底本,参照近10种版本并做出会校注释的“黄山版《红楼梦》”,应该是《红楼梦》研究与红学文化普及相结合的一次重要尝试,亦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贡献。
实际上,先生不仅是红学家,他的研究视野涉及中国古典小说的诸多研究领域。他发表的论文及尚待出版的《三国论稿》、《古典小说论丛》等著作,对明清古典小说的文本意义及其叙事传统有诸多精彩阐释;而他孜孜追索的《三国演义》之“写刘备之忠近伪,状诸葛之智近妖”,以及《水浒传》之“仇官传统与暴民土壤”的艺术与文化奥妙,深入传统文化渊源,有更多让人惊喜的创见。先生也是鲁迅研究方面的重要专家,上世纪50年代发表论文《原型在阿Q造型中的作用》,新时期出版专著《阿Q真谛》,所论远不止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这一文学形象,而是关涉鲁迅的小说、杂文、思想,关涉中国国民性研究。实际上,无论是思想观念、精神气质,还是文章风格,他都传承了地道的鲁迅风。白盾先生晚年开始研究胡适,《胡适评红的百年反思》一文在《红楼梦学刊》发表,即受到行家推重;我知道他还有《鲁迅与胡适》等诸多论文与思想,尚待整理。
先生不仅是学术家,更是思想者。早年经历战乱以至于难安书桌,中年身陷囹圄进而被废为罪民并彻底远离书房,晚年虽有书房、有书桌却无奈资料贫乏、信息稀缺、贫病交加,先生的学术生涯实在命途多舛。唯有思想无人能够剥夺,无论在人间还是在地狱都在不间断运行。所思者深,所见者明,正是白盾先生学术成就的奥妙,有限的书籍资料被他咀嚼并反刍多次,竟能从芥子之中发掘出须弥大山,从滴水之中观测到大千世界。进而,所忧者广,所虑者大,无论是《红楼梦》中诗情画意的太虚幻境,还是鲁迅锥心沥血而绘制出的鲁镇未庄,其实都只是白盾先生研读思索中国历史文化的鲜活材料,他一生真正关心并付出毕生心血的其实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之学”或“中国之谜”。他的经数十年长思精研的皇皇巨著《历史的魔道――中华帝制之谜》,就是他一生苦思的一个重要结晶。
在生活中,白盾先生是地道的书生本色、性情中人。他的书生本色,不仅在他毕生读书、写书、教书,更在他始终保持书生意气与文人风骨,其中有民国血脉,更有传统精髓。年轻时国难当头,他便以身许国,为抗日而战斗、奔走、书写;中年时欣逢百花齐放,他因忧时讽世率真直言而被划为右派、经历3年牢狱之灾,22年不得翻身;进入老年,他似乎并没有接受多少磨难经验与教训,仍是姜桂之性老而弥辣,始终保持书生的独立尊严和自由思想。一辈子清高耿介的白盾先生,与新老权贵从来都是道不同不相与谋。先生的书房兼卧室兼会客沙龙,是一些人的圣地,却是另一些人的“烤箱”。一些人来访,他会兴高采烈且极少客套,往往客人还没有落座他就已经开讲,等你坐定,他已滔滔千言;而另一些人来,话不投机,他就会长时间沉默无言,让人坐立不安,而后不得不怏怏离去。
27年前,大学毕业时被分配到安徽徽州师专中文科(现为黄山学院中文系)任教,此时白盾先生正是中文科的学术带头人,是中文科及整个学校的标志性人物。当年我们虽年少轻狂,幸而尚能热情好学,对在50年代就已成名而在新时期之初即不断有研究《红楼梦》及鲁迅小说论文发表的白盾先生早有耳闻,自然有敬仰钦慕之心。没有多久,我和几个年轻朋友就聚集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以白盾先生为核心的学术思想沙龙,话题从具体的学术讨论到一般的读书心得,再到当前中国的社会现实评析,非常广泛,几乎无所不谈。开始时,先生那一口到老不改的皖南泾县茂林村的土话让我们如闻鸟语,更何况他嗓音尖高还语速极快,稍不留神就会被抛在千里之后乃至云雾之中,简直不知所云。进而又有另一难处,即要想与他“交流”,必须有随时能够起跑、跟上然后穿插的本领。然而先生知识广博而又思想活跃,见识深刻而性情率直,饱经创伤却始终不失赤子之心,让我们由衷心折。
为了应对沙龙的交流,我们必须成为半个红学家,且必须对鲁迅的作品耳熟能详;必须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且必须有由自己思索得来的独立见解。久而久之,我们的收获可想而知。然而沙龙的收获,远不只是得先生思想言论的散珠碎玉而开蒙启窦,更在于先生的存在为我们创造了一种勇敢求索且童言无忌的“气场”,先生的思想热情如清水激流,洗刷我们的蒙昧尘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我等的思想与精神结构。他那异常简朴的书房,实是我们修行心性的道场。而白盾先生,早已为我们树立了一种智慧与精神的标杆。沙龙虽无分老少,平等自由,但若说我们都是老师,先生则是老师的老师。即使我们都当了教授,先生仍是教授的教授。很难想象,若没有白盾先生及其沙龙,我们当年的学术与精神生活会有怎样的贫乏和沉闷;而徽州师专当年若没有白盾这样的名师大家,那就实在说不出这个高校究竟“高”在何处。
当年的沙龙虽只存在了短短3年时间就因要外出继续求学而风流云散,但沙龙里学术与精神的锤炼,却影响了我们的一生。
缅怀白盾先生
白盾先生走了……
刚刚才知道这个消息,我呆坐了很久……虽然说生命终要逝去,但是在时间的长河中,用生命激起的朵朵浪花永远是那么绚烂之极。
白先生一生坎坷,学识修养皆在万万人之上,红学研究颇为精深。已是著作等身,像《红楼梦新评》、《红楼梦研究史论》早已被红学界的学人们奉为经典。87岁高龄,如今驾鹤西去,红学界又少一位人品学识都受人敬重的老人矣……
白盾先生原名吴文慧,1922年5月出生于安徽泾县茂林。黄山学院文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红楼梦学会会员。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涉及红学以来,风雨兼程,已历五十多个春秋。曾经,白先生被划为右派,关进监狱,出狱后遣回农村,前前后后20余年。在那段暗无天日的漫长岁月里,是《红楼梦》伴随着他度过了无数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历尽诸多波折,感悟人世沧桑,一部《红楼梦》也在先生的手中,翻破了,读透了……
白盾先生治学严谨,为人低调。在白先生心中,《红楼梦》既是一部“奇书”,又是一部“寻常之书”。正是因为它“奇特”,有“《春秋》之微词,史家之曲笔”才让很多人当着大谜来猜,于是红学界“妖魔毕出,神鬼乱舞”,白先生一直都不倡导如此解读《红楼梦》。
《红楼梦》被人称为“梦魇”“红魇”,让人见“易”,见“阶级斗争”。白盾先生认为,“魇”其实不在《红楼梦》中,是在读者的心里,心中有“魇”,世间一切皆是“魇”。“打破冻冰一片水,世界哪有这么多白慕大?不知的东西,源于人的主观局限,红楼一书虽杂、虽奇,也非无章可循的”。所以白盾先生更希望我们把《红楼梦》当成一部“平常之书”来阅读和享受。因为越是经典的东西,越是“平常”,越是“浅显”,越是能亲近民众。可能这就是所谓的“道不远人”吧。
红学界一直有个“传统”,我们研究《红楼梦》总是把曹雪芹捧得很高,置于云端。雪芹是天才,这无可厚非,但是让他脱离凡尘,登上神坛,让人顶礼膜拜,恐怕这样的举动并非雪芹的初衷,也并非是解读《红楼梦》的正确途径。所以白盾先生说:
尽管红楼作者曹雪芹先生作出一副“看破红尘”的架势,说什么“无立足境,方是干净”,什么“u2018好u2019就是u2018了u2019,u2018了u2019就是u2018好u2019”,什么“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什么“回风一扫,万境俱空”等等,好像身归虚无,心在寂灭,六根清净,不食人间烟火,一派“出世”模样,真个“云散水流去,寂然天地空”似的。实则他的心仍不忘宝黛情痴、人间美好,细心读者可以在字里行间领味到的。(白盾《悟红论稿――白盾论红楼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第五页)
这无疑是把雪芹还原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真人”,有了这样的认识观念,才是剖析《红楼梦》的第一步。
白盾先生对红学的贡献主要集中在红学史研究方面。2007年和汪大白先生合著《红楼争鸣两百年》就是最好的见证。这部按照时间顺序和学术流变构建起来的红学通史可谓气象恢宏。他们撰述的宗旨是:“立足世纪之初,着眼红学发展,通过红学历史进程的回顾与反思,探寻一些问题,寻求一些借鉴――亦即所谓鉴往以察今,温故而知新者也”。(白盾汪大白《红楼争鸣二百年》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二页)
这样的史学理念,是建立在当下“问题之多,性质之杂,头绪之乱,争论之烈”的现实状态下的。所以学术梳理和科学整合就成了红学研究的当务之急,也成了红学健康发展,再创辉煌的必要前提。这些学术理念对我的影响颇深。
如今白盾先生走了,带着一生的荣辱,带着对红学的一片痴情,是“好”是“了”的争论似乎没有了意义,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它源于何时,终于何方,而在于它为后人留下了一串串脚踏实地的足迹。
先生,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