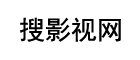项师契的个人简介
项师契,字元生,玄生,号仰平,生卒年不详。平阳蒲门(今马站蒲城乡)人,明崇祯十五年(1642)考取郡庠生。著有《三蒲综核》《蒲门志》等,均遗失。最著名的有《十禽言》组诗。
项师契的《十禽言》(并序),辛辣地讽刺抨击了清廷的残暴。《十禽言》的序言写道:“三百年之生聚,一旦俱倾;千万户之居庐,经焚而尽。况时大火流金,狂霖漂石,僵饿载道,襁负塞途。或旅处深山,喂虎之口;或颠连古渡,葬鱼之腹。甚至鬻妻卖子,委壑填沟,万种惨伤,一言难尽。”项师契的《十禽言》,“聊托鸟语”(十禽十语,即“男言”、“女言”各五首),倾诉了乡亲颠沛流离的凄苦和怨恨,饱含着对乡亲的深切同情,真可谓字字血,声声泪,感人至深。
基本内容
出身世家,豪爽亦多才
据苍南《瀛桥项氏宗谱》记载:苍南项氏系晋时从福建长溪赤岸(今霞浦县境内)迁来,原籍蕃盛。始祖项昭自五季晋高祖朝任大理评事,为避战乱,天福六年(941)辛丑,闽王曦僭乱,战无宁日,乃弃官徙居浙江温州府昆阳金舟乡瀛桥西堡(今钱库镇项家桥),相其地势,倚山临海皆得其宜,遂家焉。后裔得以繁衍各地。至十三世项文弥,于明洪武二十三年与孙存道同调至金乡卫蒲门所第十五军,始迁来蒲门定居。其孙项存道,字耕读,始创以田园三百亩开塾办学。时值明朝开国之初,地方上无学堂,一经办起即收学生数百人,金乡一带世家子弟纷纷负笈受业,名望甚高。
项师契为项文弥第十世孙,字元生,号仰平,明崇祯十五年(1642)考取郡庠生。其祖项琳,字本玉,号荆石,例授礼部儒士。其父项澄海,字清之,号平阶,邑庠生,为人刚直豪放,中年多置台榭花鸟,拥有千余亩良田,时家住蒲门东门街,有房屋70余间,当时有“蒲门半条街”之称。清初迁界时项家产业均毁于火,祖业已渐凋零,后裔亦零落各地。自项师契后历二世,子嗣凋敝,后景凄惶。著有《三蒲综核》《蒲门志》等,均遗失。
亲历浩劫写下《十禽言》
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政府为阻断郑成功率领的水师同沿海居民的联系,断然决定实行大规模的强制迁徙濒海居民的政策,史称“迁海”。清政府对威胁最大的福建以及同福建相邻的广东、浙江三省视为重点迁海省份,因而迁界令执行得最严格的也是此三省。清政府文过饰非把迁海说成是一项关心民瘼的德政,如开始迁海时,清廷在上谕中说:“前因江南、浙江、福建、广东濒海地方,逼近贼巢,海逆不时侵犯,以致生民不获宁宇,故尽令迁移内地,实为保全民生。”其实,对广大民众而言,迁海自始至终都是以野蛮的方式摧残沿海居民的一场暴行。项元生因为亲历这场浩劫,满腔悲愤地写下这首诗,这首诗因其触发了时代的痛点,记录了真实的场景而被同时代及后辈文人转载保存,流传至今。
在浙江执行迁界令的背景下,原平阳境内(包括今属苍南的金乡、蒲门)的居民被迫内迁十至三十余里。顺治十八年夏,温州副总兵张思达率大兵进入平阳县境,插木为界,界外房屋全部烧毁,居民四万多人被迫离乡背井,悲号流离,惨不忍睹。失去了家园的迁民们当时的命运犹如蝼蚁、泥沙,任人践踏,软弱者受尽欺辱,强悍者则铤而走险。后来,迫于生存,一部分迁民参加了郑氏义师,或在当地揭竿而起。还有一部分迁民在内地无法谋生又不甘心坐以待毙,就砍人树木,伐人坟墓,偷盗抢劫,为所欲为。
由于在实际实行过程中的粗暴手段和受命官吏的飞扬跋扈,迁海给沿海居民造成的灾难是巨大的。因迁界导致渔民不能捕鱼,盐民不能晒盐,农民不能耕田,不愿意离开土地的往往就地被杀,入界后因生活无依靠,饥死病死不计其数。项元生由于亲历这一场浩劫,“聊托鸟语向三春以哀鸣”,悲愤地写下《十禽言》组诗。
《十禽言》共十首。其一为《播种百谷》:八口十口须食足。弃膏腴,焚积谷,流落偷生佃南陌。秧针未下先定租,不管年荒与年熟。快着意,播种百谷。
其二为《借屋住住》:灶房卧房共一处。地为床,衣作被,居停之居神佛座。父母妻儿共坐眠,相看泪珠浑如注。哪里去,借屋住住。
其三为《提葫芦》:酒虽爱饮要钱沽。非宴乐,莫呼卢,充馔嘉肴溪蕨蔬。千愁万恨推不去,付之一醉假模糊。勉强提葫芦。
其四为《脱却布裤》:裤若脱了丑便露。机杼纱,刀尺布,裁就中衣针线做。悬釜专待米来炊,博得一餐也不顾。只得脱却布裤。
其五为《不如归去》:家在昆阳尽头处。为海氛,罹播弃,哀鸣中露无家计。南鸟焚巢归北林,羽毛零落飞何树?谁敢说,不如归去。(以上五首为男言)
其六为《行不动也哥哥》:山路羊肠多坎坷。含羞耻,逐奔波,鞋弓袜小越关河。深闺不出涉远道,当此流离怎奈何?实行不动也哥哥。
其七为《泥滑滑》:淤泥遍地泞罗袜。冒炎霖,忍饥渴,袅娜身儿挨跋涉。一步一跌苦难禁,不如坐此凭他杀。免得这,泥滑滑。
其八为《咳苦苦》:这村不住搬哪都?没柴米,缺韭蔬,仰面告人颜先无。冷暖世情通相似,患难谁肯来相扶。徒自,咳苦苦!
其九为《天花发》:春来红紫满头插。逞轻盈,媚风月,不须对镜浓涂抹。此来憔悴懒梳妆,只把青纱束飞发。休听它,天花发。
其十为《交交桑扈》:桑在故园人在路。慎三眠,勤九度,蚕丝抽织绮罗富。于今百结不蔽身,谁想养蚕炫裙布。漫劳呼,交交桑扈。(以上五首为女言)
以鸟喻人,
反映民众悲苦
《十禽言》中,经查阅有关资料:《播种百谷》《脱却布裤》指布谷鸟,《借屋住住》指燕子,《提葫芦》指提壶鸟,《不如归去》指杜鹃,《行不动也哥哥》指鹧鸪,《泥滑滑》指竹鸡,《咳苦苦》应是姑恶鸟,《交交桑扈》应是青雀,《天花发》不详所指。《播种百谷》等五首男言以男迁民的口吻进行叙述,讲述迁界以来遭受的悲与苦。不如归去,却又如何归去,美好家园已尽失,回乡之路,惨云愁雾沉沉笼罩。其实,受迁界之苦之痛最深的莫过于从未出过远门的女人们,《行不动也哥哥》等五首女言以女迁民的感受痛述其间悲与苦。
曾经,在蒲城代代流传的民谣中有一首是《三条岭》:“妈啊妈,囡儿不嫁江南啊妈,三条岭,四条长。”从未出过远门的年轻女子,尚且知道这三条岭通天长,足见其“行路难”之甚,故此素来有“浙南蜀道”之称。蒲门三条岭的艰难险阻,令人生畏,望而却步。“含羞耻,逐奔波,鞋弓袜小越关河。”而此时的女人们为生存,不惜抛头露面,弓着小脚和男人们奔波逃命在难于上青天的古道之上,一路忍受颠沛流离,愁云惨雾。“冒炎霖,忍饥渴,袅娜身儿挨跋涉,一步一跌苦难禁,不如坐此凭他杀。”一路的风餐露宿,炎炎酷暑中,长途跋涉,走一步跌一步,后路已断,家园已毁,前路漫漫,生死未卜,苦不堪言,绝望之情溢于言表。“没柴米,缺韭蔬,仰面告人颜先无。冷暖世情通相似,患难谁肯来相扶。”身在异地他乡,举目无亲,生活无着落,深深感受到世态炎凉,前途无望之悲凉。曾经是“逞轻盈,媚风月,不须对镜浓涂抹。”的姣好容颜,到如今是“此来憔悴懒梳妆,只把青纱束飞发。”备受生活折磨,哪里顾得上梳妆打扮,只能听凭这无情的风霜将红颜摧残。怀想当时“慎三眠,勤九度;蚕丝抽织绮罗富”的安逸生活,到如今却已是“百结不蔽身,谁想养蚕炫裙布。”回想从前悲叹如今“桑在故园人在路”,不由更令人感伤不已。声声泪,字字血,虽然时隔数百年之后,字里行间的悲愤依然穿透时空,将那一份哀伤与惨淡遥遥传递,深深撼动人心。
在《十禽言》序里,项元生记录了迁居时的悲惨情景:“三百年之生聚,一旦俱倾;十万户之居庐,经燹而尽。况时大火流金,狂霖漂石,僵饿载道,襁负塞途。或旅处深山,喂虎之口;或颠连古渡,葬鱼之腹。甚至鬻妻卖子,委壑填沟,万种惨伤,一言难尽。”
诗与序叙述倾诉了颠沛流离的凄苦和怨恨,饱含着对乡亲的深切同情以及对清廷的控诉,声泪俱下,痛切心肺。在外有倭寇入城抢杀掠夺,内有贪官污吏横行霸道,鱼肉百姓,使广大的人民受尽了折磨和苦难,生活负担已经相当沉重的情况下,又要遭遇迁界,对蒲门民生来说这无异是雪上加霜。在强制迁界的命令下,民众只好背井离乡,一夜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一路的颠沛流离,翻山越岭,饥寒交迫,风餐露宿,饿死的,病死的,落入虎狼之口的时有发生,很多暴尸在沿路途上却无法及时掩埋。后又因渡轮事件,由于船少人多,严重超载而发生了沉船惨案,很多人葬身鱼腹。当幸存的人们好不容易一路凄惶之中跌跌撞撞来到那举目无亲的地方,在露天地里埋锅做饭,夜间蜷缩在他人的屋檐下、破庙里饱受风霜摧残,男人们唉声叹气,女人们哭哭啼啼。生活艰难,回乡无望,家破人亡,因而,迁界之初,夜深人静时,常有跳河的,上吊的,自行了断之事屡有发生。迁界时值夏季炎炎,蚊子、苍蝇、跳蚤、老鼠横行乡里,加上饿殍遍野,引发恶疾肆虐,更加深了饱经风露摧残迁民们身心健康,导致人人大放悲声,四野哀啼。
康熙九年(1670),清廷下令“展界复井”,恢复界外地,允许原沿海居民回乡耕种,蒲门一带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却延迟至康熙二十三年台湾收复后才复界。迁海政策给沿海居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也给清政府自身带来了重重困难,却对郑成功领导的义师并没有起到多大的威胁和阻挡作用。蒲门的军事防卫功能在明代抗倭期间发挥得淋漓尽致,然而随着逐渐平定倭患,迁界之后的蒲门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一度作为浙闽交界的文化经济重镇的辉煌也不再,很多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资料也在此劫难中被毁,永远流失。